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裡,我們宇宙萬物的變動都是一個連結著另一個。摧毀到重新建立,瀕臨滅絕到興盛泛濫,這是亙古不變,難以打破的循環。在這反覆的過程中世間萬物卻發生了許多更迭,不管是不可逆的變化,還是周而復始的進化。我們如同水,轉型成不曾想過的樣態。
時間如同洪流,帶領我們往前邁進並沖淡過往留下的痕跡。
水的流速越來越快,靈魂與肉體之間的手被沖開了也沒注意到。
但現在像是被引進人造水壩般,開始停滯不前時,回頭去看,麻痺的知覺才逐漸回籠。缺陷與溢出,在擁有的片刻沒想過是用什麼換取來的。伊卡洛斯的翅膀在藍天為他帶來驕傲與喜悅,卻忘了緊繫生命的蠟翼正在融化。
在只注意前方的時候,我們捨棄了什麼?
幼蟲與若蟲。同樣經歷蛻變的時刻,但兩者之間只相差結蛹的過程,
而凝結出的結果截然不同。好運討喜的瓢蟲與擅於偽裝的竹節蟲,我們在改變的同時,不知是否其實是想掩蓋住自己的缺陷。
這些導演與演員們,他們想透過電影跟我們這一世代傳達的訊息。不管是心路歷程還是自我探索,他們都透過攝影機,赤裸的展示在螢幕上。有時是想為在自我掙扎的青少年搭把手,而有時是為迷惘的雛鳥做導引。他們的用心,你會在低下頭去看自己留下的腳印時發現。
看著《 早餐俱樂部 》(英語: The Breakfast Club)的時候,會不自覺地想要吃培根、炒蛋、鬆餅與很多很多的砂糖。一部上映於1985年的青春校園喜劇電影。由約翰·休斯執導與編劇。講述五個青少年因為留校察看而在過程中互相磨合的故事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長背景和社會角色,卻自相矛盾著。
「你認為自己是誰?」
這是副校長維儂先生作為對他們這些壞學生的懲罰,指定每人要交出千字的作業。「資優生」(brain)布萊恩、「運動員」(athele)安德魯、「神經病」( basket case)愛莉森、「公主」(princess)克萊兒和 「罪犯」(criminal)約翰。大家都因為各自犯下的錯誤來到星期六早晨的圖書館,他們當然是沒有乖乖的把作業做完,甚至偷溜出去拿大麻回來抽。在一連串的衝突、談論和聆聽放鬆音樂下(我相信一定是因為加了大麻),他們逐漸卸下心房講述自己的生活。
在外是萬人迷,但回到家要面臨雙親的爭吵;在外無惡不作,卻在父親家暴母親時無能為力;活在長輩的期待中,如同機器人般無自由意識;成績突然考差,而被責備所以想自殺;遭受到親人的冷暴力,無法控制偷竊的習慣,希望引起注意。
雖然現今社會越來越進步,我們被家庭的影響卻沒有減少。
每個人會成為現在的樣子,大多是因為外在的影響。自己可以決定想成為怎樣的人,卻不能在路途中缺少崇拜或是學習的對象。在這個年紀階段,其實已經可以清楚的判斷絕對的對與錯,不過還是有走在灰色地帶的時候。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就很重要,它可以讓我們獲得被愛與歸屬感,並向他人釋出愛與尊重。當周遭環境讓人無法舒適的做自己時,我們就會選擇戴上偽裝的面具。如同竹節蟲,順應自然,隱藏真心。
在電影結尾,五個人都了解不同的彼此,跟更加認識與堅定自己的原樣。雖然友情可能會隨著今天的結束而淡釋,但他們從明天開始會用不曾用過的視角去看待同年齡的其他人。身為資優生的布萊恩被指派完成文章,剩下的人回到原本的位子準備迎來他們的結局。也是全新的開始。
順應自然的時候保持真心。自己同時不等於又等於任何的定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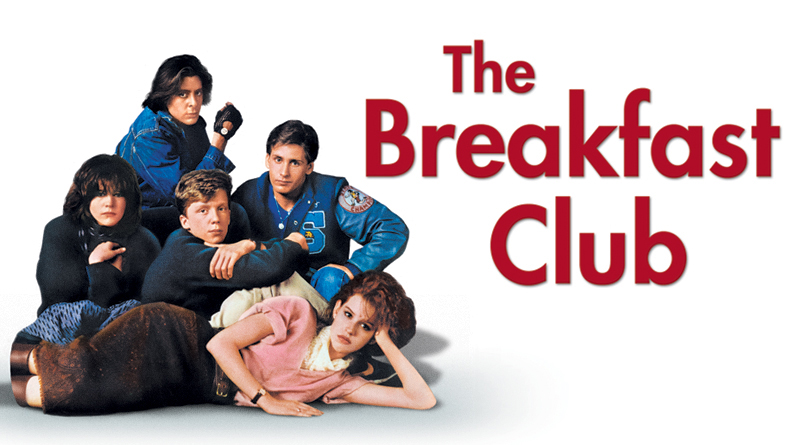
「我們每個人都是資優生,運動員,神經病,公主和罪犯。這能回答你的問題嗎?
———真誠的我們,早餐俱樂部」
當我們面對人生全新的抉擇處境時,你會選擇大膽的一躍而下,還是退縮回到原本平鋪的道路呢?
在暖黃與冰藍色調的加拿大中。麥特在冷清的早晨跳進湖裡,貌似追尋著明確的目標,但卻在途中失溫、溺沒、落下;麥斯在和著血的玻璃中,看著自己血紅的倒映,這是他想要的嗎,失落、離去、缺憾。風從指縫中溜過,但帶走的不只有指尖上的餘煙,還有紊亂的思緒。
一部電影、一次差錯的親密碰觸,會對你的生活帶來多大的擾動?
麥特目前三十歲的生活還挺舒適的,看似美好光景的底下,掩蓋著複雜的情緒。愛與被愛、分與離跟想要與需要。所有事物糾結在一起,一切在兒時同伴麥斯即將遠渡重洋去澳洲展開新篇章時被翻起,面對這不說明的曖昧處境,他不知如何對待。
在《麥特與麥斯》(英語:matthias and maxime )中,導演扎維耶.多藍利用紅與藍兩種鮮明的顏色傳達出碰撞與治癒,有著明確的定義與邊界,卻在生活中交織著。
在我們的認知中,藍色如同寒冰麻痺裏外的接觸,紅色如火焰般使冰冷的感知暖和。但電影所帶出的感覺卻不完全相同,腥紅的憤怒遮蔽自己的思緒,只能記得悲憤。蔚藍的平靜包裹自己的四周,像是徐徐微風撫平燥熱的皮膚,什麼也沒留下。
麥特的自我懷疑與小題大作,顯示他其實被受煎熬許久。自己內心的聲音在嘮嘮敘敘,選擇不聽、不看和不想,緊閉的心房還是會有鬆動的那一天。麥斯與家人間的摩擦跟愛護攪混在一起,想要理也理不清。偏愛與忽略對於每個年齡層的人來說,都是件難以治療癒合的事。
自己到底喜歡什麼,可是真正要的東西卻不一定相同。在每一天過活當中,總是在尋找著自以為缺少的部分:少了對生活的動力,少了對事物的熱情,少了對他人的愛戀。但有時在越過重重迷霧後,發現問題也隨著天上照下的陽光煙消雲散。

「每個人對自己都有疑問,這就是青春的美妙之處。」
「你才這麼年輕,還有大好人生等在前方。」
父母是帶領我們到這世界的嚮導,他們走在一直走在前方,直到身後的腳步逐漸穿越過自己。而我們在未來的某一天也可能將成為父母或者是引領後輩的指路者,將負起責任直到重覆之前的循環。在這條道路的過程中,我們將面對很多的辛勞與失落,甚至是走投無路,但事情是否真的是我們想的這樣?
在千萬的平行宇宙中,就有千萬個自己。《媽的多重宇宙》
(英語: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)的主角艾芙琳在平乏的生活中要同時擔當好幾個角色,扛起重擔的一家之主、嘗試理解女兒的媽媽、讓父母失望的女兒等……壓力囤積在體內無處可發,她無法與他人訴說,也或者是她也沒想過可以這麼做。但在準備去處理稅務,碰到自稱是來自另一個平行時空的丈夫時,日子中看似無法解釋的事情都有了答案。
由身為華裔關家永與好友丹尼爾·舒奈特一起編導。講述舉家移民到地球另一邊的華人,去追求存在虛實之間的美國夢,裡面參雜了想被認可、勇於冒險與逃避責任之類的複雜情緒在裏頭,如同加了過多勾芡粉的羹湯般,稠稠糊糊的,在十分噁心與十分享受的兩端臨界值跳動。(還是只有我覺得這類型的食物很好吃?)
這幾年常在網上能看見許多關於華人家庭結構的自嘲和討論,不外乎就是在講不坦率的愛跟「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」的教育。在外人來看,尖酸刻薄的傷人語句對著摯親說是無法想像的事。被觸碰的含羞草會緊閉枝葉直到再次回復,在我們認知的解碼下,一字一句之下是說不出口的的愛或者是彆扭的關心。
最令人感到心被揪住時,是看著媽媽與女兒真正對話的時候。當忽然得到對方的認可,發現預想的釋然與喜樂並沒有雖知道來,而是覺得只是被認可「表面」,不是「本質」。
父女之間、夫妻之間還是母女之間,名為「親情」的紐帶絞緊拉扯。令人覺得刺痛到無法接受卻又不能放手,在渴望的同時又想拒之千外,仙人掌的刺雖然扎人,但剛長出的新刺卻是柔軟的,會讓人忘記被傷害的感覺。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中,覺得自己應該逃離這不健康的關係,可置身事外時才發現沒察覺的錯誤。
那個錯誤就是,不知道自己其實沒有錯。
學習失敗,認識挫折是令人心累的事。但沒有這些缺口,我們要怎麼變成更好的自己?

「人生中的每個拒絕,每個失敗,都成就了此刻的你。」
當自己注意到缺陷的時候,會選擇掩蓋住或者是填補,不管是哪一個我們都沒有真正的接受自己。但是當我們去選擇改變時,一切就變得不同了。新的視野、型態與思考,衝擊並重組成更進階的樣貌。
電影從被發明時就是個媒介,可以藉由鏡頭與影像播放傳遞給世人訊息。不管是悲傷的還是快樂的,我們希望觀賞者感受到想被傳達的意念或者是想法。在無意間讓人找到他們缺少的東西,或者是改變了自己的觀點。
在全黑的空間裡面,那投射出的唯一光線中。讓不同的靈魂相互融合交換,滲渡過彼此所需的,最後隨著電影的尾聲回到各自的肉體裡。
這就為什麼我深愛著電影,因為可以變化成多種樣態。
「取捨」一直以來都是個無法略過的步驟。沒有失去我們又要如何去獲得?所以與其為空白哀悼,不如去為新增而歡喜。雛鳥剛從安適的卵殼破出時,也是顫抖著身子,努力向這世界發出牠的第一聲啼叫。
在完全變態與不完全變態之間,也許從瓢蟲的蛹裡破殼而出的,是一隻緩慢行走的竹節蟲。
隨時一動也不動,隱匿在這繽紛的世界也挺好的吧。
———特別感謝 台南高商 電影欣賞社社長 黃婭菲 撰文」